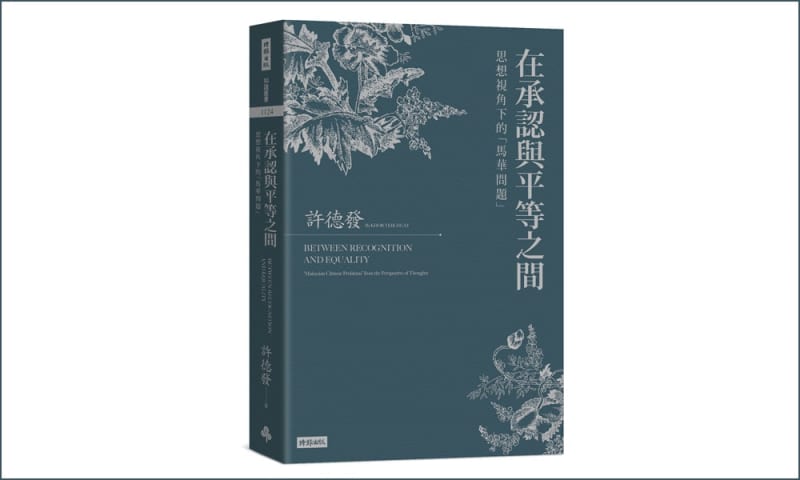
【精选书摘】
本书主要整理、修订与结集自笔者于2006至2016年十年间所写就的有关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想与文化论文。2006年从新加坡国立大学提交博士论文后回到华社研究中心复职,笔者有幸参与了《马来西亚华人与国家建构》研究计划,是以,开始围绕著相关议题撰写了这些原本都是独立的单篇论文。其中在这十年间发生的政治发展,尤其是2008年大选之后所牵引出的问题与争议亦成了本书思考的面向,形成了本书的思考既是历史的,亦是现实的。
然而,这些论文都是在同一个思路与关怀下撰写的,甚至中心思想亦离不开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核心问题,并尝试追寻问题的基本根源,及探析在这一问题脉络下华人社会文化的限制、型态与社群建构。
这里所谓的问题,其实是犹如林毓生教授所谓的“问题丛聚”(problematiques),即不是单一的问题,而是指谓一连串或一组相关相扣的问题(林毓生,2019: 420)。也就是说,本书各章节基本上可说是相关问题的开展、或侧写或综论或横述,但背后的关怀是一贯的,即便思路与方法也是相同的。首先,这里有必要对本书各章思路与研究途径略作阐述。
一、危机意识、“平等叙述”与“马华问题”的根源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现代重大变迁,始于二战之后。马来民族主义的崛起、国共内战、中共上台、紧急状态及独立解放运动以至独立建国之发生,大体都形塑了华人乃至整体马来西亚的当下。对笔者而言,身处于马来西亚,这几乎命定了吾辈必须思索“马华问题”、为其纠结,甚至这是跨代华人的共同命运。因此更具体说,本书所收各章大多虽成于过去十年中,但许多思考则远自于作为一介普通华人与生而来的日常处境,是一种来自于对自身生存语境的感受与自省。
从历史角度来看,自一九五○年代马来西亚华人进入独立运动时期之后,那种“感时忧国”的精神逐渐发展成了马华社会的初始性格,“忧患意识”也变成了一种永恒的基调,甚至于贯穿了华人社会自独立以来的各种大小事件。
张灏曾经在一篇演讲中谈到近代中国人的“危机意识”与危机发生的时间节奏有关(张灏,2002年4月27日)。他指出,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是一种“慢性病”,他们十年、二十年来一次,主要目的是经济上的榨取,不是领土上的掠夺和军事上的佔领。但是到了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慢性病”却骤然变为“急性病”。
具体到马来西亚华人而论,自独立以来,其社会一直是一个不断受挫的群体,置华人社会于不利与存亡窘境的政策与事件接踵而至,这表明华人社会危机的速率也是相当高的。在面临这些繁复丛生的危机时,一股不安的情绪一直都在社会中流动,也使得这个社会总不能完全安顿下来。然而与“危机意识”的频率快速的情形相悖反,“马华问题”之解决却呈现出一种“慢节奏”的态势,甚至于问题又有不断深化之势,新旧问题相互迭现交集。
实际上,独立前华团领袖刘伯群针对宪法制定的疾呼最能反映这一“危机意识”,他当时高呼:“全马华人已面临了最后关头,如不及时争取,恐已无机会了。”这是刘氏在华人团体会议上议决远赴英伦争取宪法平等时所说的话。据当时的新闻报导,华团会议已深知他们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
经过冗长时间之讨论,(会议)乃认为目前本邦华人已面临了生死关头,非从速派出代表团赴英向英廷力争平等待遇不可。为了我们下一代,为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非力争不可。(马团工委会力争宪制四大要求 决派代表团赴英请愿 郑重声明马华公会仅为普通政党 不能代表全马华人公意,1957)
所谓“生死关头”深切道出了他们心中的焦虑与紧迫,这一英伦之行可谓乃华人社会尝试从根本上解决族群不平等问题,但最后以失败告终。以上这一会议言辞值得加以援引(本书也一再引述),因为它标志著现代华人社会沿袭超过半个世纪之“危机叙事”的最初表述,而且也揭示了华人危机意识的根本核心源头——即“平等”仍是未解决的优先问题,自此亦形成了华人的“平等叙事”。
“马华问题”之大者,实际上即是“族群平等”问题,并由此延伸至自身社群之文化与社会建构的困扰。可以这么说,从独立宪制谈判与政治博弈开始,国家(state)与华人民间社会之间的代沟日益增大,这是“马华问题”丛聚的另一面向。
独立至今数十年中,华人命运多舛,遭际叫人太深沉,国家却始终未能改弦易辙,华人的危机心态也一直在沉积之中。尤其是1969年五一三事件遭遇流血教训之后,华人的危机意识可谓达到了极点。
步入惨剧之后的一九七○至八○年代,华人大体已知“可为者”已不多,然而伴随著新经济政策、国家文化政策、大学名额制、工业协调法令等一系列不平等事件,却是华人社会一场又一场或许不到“壮阔”,但绝对是“激情”的政治与文化运动。在这二十年间,华人社会从徬徨到反叛,经历了全国华团文化大会、华团宣言、合作社集资运动,再到政治上的民权之提倡、两线政治的追求、华团参政等,但明显的,整个七○、八○年代的实际政治实践结果并不理想。
著名政治学者何启良当时即指出,“八○年代开始,更有种族两极化现象的产生。许多分析家以为,即使2020经济宏愿能够如期达致,国内种族权益的不平衡状况似乎在可预期的未来不可能扭转,华裔公民的地位亦不会有多大正面的改变;反而,各种迹象皆显示了大马华人政治边缘化的趋势”(何启良,1994: ii)。一九九○年代以后,从华人对人口比率急速下降的焦虑反应可知,华人的危机意识犹在,但形势比人强,华人已经察觉自身的“无力回天”。
与1969年以前兴起的反对政治与左翼政治狂飙相比,华人对政治丧失了比较积极进取的态势,并转向一种消极的“认命”意识。经历大半世纪之后,一般华人在政治期待上趋向于保守、悲观,甚至移民、出走,据郑乃平指出,独立至一九九○年代已有上百万华人移居他处,相当于今日华人人口的约15%强。
许多人大概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上感受到华人社会这股或许可称为“前所未有”的“大局底定”情绪,他们深刻怀疑自身在马来西亚的前途。当然,自2008年三○八的“意外选情”至2018年五○九“意外变天”之间,华人社会从意外、低沉到兴奋的循环中似乎有了命运的转折,但2020年之希盟“意外倒台”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点,这是后话。
马来西亚华人的这种感时忧国的时代精神辐射极大,除了贯穿于华人政治、社团组织,它也都反映在文学、文化与学术各层面上。夏志清曾针对中国现代文学指出,近代中国感时忧国的精神传统使得中国作家把主要目光集中到文学的内容而不是形式上,即集中到得天独厚的“现实主义”上(夏志清,1979: 17)。
谈到马华文学,马华问题也同样把作家们长期收拢到现实主义的怀抱之中。在学术研究上,议题则呈现不断当下化的归趋,这与一九五○年代“南洋学会”诸人如许云樵、姚楠等学人纯粹注重南洋的风土历史有极大的差距。实际上,危机的解决是与观念的形成相互对应的。
危机意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使自身对周边世界的认知态度发生改变,并形成新的观念力量。但是,由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结构性的困局使然,学术领域自身还远未形成一股具有独立规范的领域与建制力量,而且未能出现有创造性的论述以引导社会,使得马华人虽有一种强烈的现实感,学术与社会却基本无涉,危机意识自无相应的实际对应。
对马来西亚华人而言,可以预见的是,本世纪将依旧可见他们踽踽寻思出路的身影(以上可详见许德发,2007a: 7-10)。简言之,要了解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及其各领域之发展,几乎不可不理解造成其忧患的“马华问题”。
二、思想史途径、自由主义视角与“马华问题”丛聚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马华社会存有其特殊的“基本问题”,这一马华问题纠结了几代人,也正如前述,它是一个问题丛聚。概括的说,华人问题的根源笔者将之归结为土著“原地主义”,而这其中回避不了族群主义、与国家的关系以及宪法诸问题之纠葛。“原地主义”的题中必有之义必然又带来了不平等与正义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政经文教困境。读者当可从本书中看到这些关键词的连贯交错。
所谓“基本问题”在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看来,是不可能解决的,从而诱使知识份子不断地深化他们对各自国族问题的理解,并设法去解决之,比如德国人曾受“德国人不是二等法国人”的“德国问题”困扰,近代中国更有其“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中国问题”(参阅汪丁丁,1997:38-42)。
以林毓生的概念,他在解释problematiques这一词汇时,亦尝译为“无法获得确解的问题”,这意即“马华社会问题”就是一个如此的复杂境况——既相互纠结,亦无法确解。当问题永远不能解决并且永远成为问题时,一个社会的聚焦点乃至看待问题、提出问题的方式与观念传统——“问题意识”于焉形成。
此处所谓“意识”是一种“自觉”,而“问题意识”(problematic)意指“自觉于自己所提出及要解决的问题”。此一自觉来自于自身所具备的一套基本想法与思路。问题意识的养成,可说取决于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基本问题,因此釐清“马华问题”洵为重要(许德发,2000: 2)。
对笔者而言,这样的“问题意识”实有两个层面的意义:首先是作为身在其中的研究人员观察问题的意识与态度,即作为一个马华社会中文学术人员——笔者念兹在兹的关怀。这个问题意识使一位研究者能自觉于学术研究课题与自身生存机遇之连接,
正如沟口雄三所质问的那样,他说“在日本的中国研究者中,不断对自己追问下面这个问题的人并不很多:我们日本人研究中国的作品和文献意义何在?准确地说,追问的人是极为少见的。而竹内好,是这极为少见的追问者之一。比如,他曾经在一九四○年2月的《中国文学月报》中写文章批判后来成为中国古典文学大家的目加田诚,揶揄说他过著‘每天早上夹著皮包到支那文学事务所去上班的生活’”(沟口雄三,2005: 82-87)。
但上述日本情境毕竟还隔著一个以中国作为其媒介的中间物,再进而把现代日本“问题化”,但马华问题于吾辈而言,其“问题化”却是那么的真切与自动化。
第二层面的意义在于“马华问题意识”作为一种研究对象与观察方法。本书的基本题旨即在于寻绎一系列马来西亚华人的问题及其原因与历史过程,意即笔者尝试做“起源学”(genetic method)的溯述,企图以此一方法去思考问题和求證过去。
所谓“起源学”可归属于历史的范畴,它主要从本质与根本的角度探讨现象发生及其之所以得以存在的关键因素及过程,尤其追问现象或事物最初发生以及之后持续存在的动力。易言之,本书尝试捕捉马华问题的根源,以及引发这现象的背后关键动力。
此一取径方式与笔者的现代思想史训练有关,就如斯特龙伯格(Roland N. Stromberg)在著述《西方现代思想史》(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一书中所说的:“思想史研究者通常坚信,任何一个时代(各个时代不同)都有一种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影响著思想和表达的所有领域”(斯特龙伯格,2005: 5-7)。他进而认为,思想史应该揭示思想发生的语境,显示这些思想是如何在大文化语境中相互联系。我们必须具备一种发生学的意识,把最具关键意义的时代特征、事件与思想言论加以贯通,点明它们之间的逻辑与因果关系。
显然,马华社会语境自有其时代特征,因此其问题的形成自然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生成的。故此,要追溯与理解马华社会问题及其形成过程,我们必须把它置放于马来西亚特殊格局中加以考察,尊重问题本身在脉络中的显现。我们首先必须追问华人社会所对应的语境是什么,而这个语境又为他们形成怎样的问题意识。
如上所述,问题意识乃一种对所寻求解答的意向上的引导,它总是指向一些基本问题。对当时关怀局势者而言,他们主要关心的是社会中存在的基本问题,他们为基本问题而感到焦虑和冲动。而对基本问题的把握,往往必须依靠一种时刻围绕著他们的氛围。那需要一种直觉、一种对应与基本问题相关的一切问题和一切事物的敏感性(汪丁丁,1997:38-42)。
每一个时代其实都有各自的问题意识,许多思想与思索便是在这个背景下进行的。显而易见,当下的问题是一个决定他们如何走下一步的其中一大关键。不从此处著眼,就看不到也感受不到他们的感受与所思所想了。有时问题之所在,其实就是答案之所在。
故此,本书将尝试揭示当时人所梳理的、认知的、眼中的马华社会基本问题以及问题意识。从历史角度来说,过去各时代都有它特定的善恶标准,以及身处其时的特有感受。当时代氛围随著事过境迁而消散时,人们就不再掌握当时人对事件的真实感受。我们这一代人的感受不会比他们来得真确。
历史评价一方面要求距离感,另一方面要求在重返历史现场之基础上,了解以前的人是怎样感受的,而切忌以今天时代的标准或局面去断定或控诉过去。有时通过当时人的问题意识或能彰显从资料条文中难以显现的语境,它不仅有助于解开文本语意,更重要的是展现了文本以外的实情与氛围,从而为深入一步理解历史的真实提供了密钥,不至于为后视的各种意见笼罩与遮蔽。
因此,本书资料尤重当时的报刊资料,以还原或更接近当时人的舆论氛围及他们的心态。自近代中国改良与革命之争延伸至马来亚以来,中文报刊成为了两派的宣传重地,但报刊自二战之后,逐渐将关怀重心转向本地社会,并成为马来亚华人的喉舌、华人社会三大支柱之一。故此,通过华文报刊,我们可以显见华人社会的时代脉动与精神。
实际上,近代报刊理论中影响最深的是哈伯玛斯(Jürgen Habermas)所提出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他指出,此一“公共领域”包含实质空间(如咖啡店)与抽象空间如报刊,而其“公共性”使得各阶层的意见得以反应。
必须指出的,马华社会是本研究的“客体对象”,而中文报刊可提供我们理解当时此一“客体对象”所身处的氛围及其反应,但不代表笔者认为报刊中的见解或报导是完全真实可信的。相反地,笔者将借鉴其他相关研究以互證历史的事实。
因此,本书基本上仍旧是历史学的,并兼以思想史视角切入问题,因此书中所援引的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学说及其视角,主要是从思想角度出发,希望藉此庶机可更深入揭示马华政治与历史问题,开拓马华研究的视野。此书因此并非政治学或政治哲学著述,自然无意跟随政治哲学或自由主义的研究典范去开展问题。
笔者主要是不满意于现有的相关历史研究之纯粹客观陈述,因为它显然无法解释或回应马来西亚与华人所积累的政治现实与历史问题。晚近几十年来,对应于美国及西方的社会变化,自由主义发展出了回应社会不公的“平等自由主义”,以及回应多元认同与文化族群的多元文化主义。
“平等自由主义”这一由罗尔斯(John Rawls)所主张与开展的自由主义基于回应西方世界的社会不平等状况,强调“机会平等”,关注起点的平等,但又同时坚持效率优先(约翰‧罗尔斯,1988)。在罗尔斯的理论下,“处境最不利者”是他差别原则论述的适用对象,而他的社会契约论、反思平衡的方法,及其所追求的良序社会目标,恰恰是要在多元社会中寻求关于社会基本结构的原则共识。
这一点特别重要,它最能启示于马来西亚这一价值分歧问题严重的多元社会,尤其是针对马来西亚的扶弱政策与土著主义。马来西亚各族间的价值分歧,如特殊地位vs普遍公民权、历史统绪vs平等价值等是本书特别关怀的。笔者认为,必须承认马来西亚的一些价值分歧与纷呈是“无法通约共量”(incommensurable)的,甚至是本质上的,故此本书援引了另一位自由主义学者格雷(John Gray)的“暂定协议”(modus vivendi),加以论述了马来西亚独立宪法之拟定(详见第二章)。这其实也说明本书对华人或马来人的基本立场,即两者之间的一些价值矛盾与分歧并非是完全对错分明的。
然而,由于马来西亚特殊的历史与现实语境之不可复制,美国或西方国家的某一个理论并非可以完全对应的。比如,马来西亚面对的问题并非纯粹“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等问题,更是多族群之间、原住民与移民之间,或者如金里卡(Will Kymlicka)所说的,是“文化社群”之间的问题,也就是“认同差异”的问题,而非个人自由主义论述可完全对应的。
犹如以上所略述那样,在马来“原地主义”主张底下,马来民族主义者认为移民与土著之间的“差异”造成国民之间不能平等,马来人因此获得特别权利。易言之,马来西亚的权利载体(rights-holder)一部份在于族群,而非个人,其不平等待遇是集体性的、制度性的,因此从自由主义内部回应多元文化主义挑战的金卡里之论述值得借鉴。
实际上,笔者讨论社群权利并非否定普遍的自由人权概念,只是认为社群权利论述有利于马来西亚的普遍平等权利之追求。作为自由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家的金里卡,他尝试以“多元文化公民资格”(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文化权”等概念取代或补充自由主义传统中的普遍公民与普世人权概念。
在金里卡的论述中,他认为自由主义和文化权利、族群差异等概念并不冲突,自由主义的个人应该被看成是某一个文化社群的个人,其所具有之文化身份是一项基本的善(good),因此文化社群必须被尊重(2005b:173)。虽然,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我选择价值的重要性,但是任何个人的选择都是从我们认为有价值的选项(options)中进行,而选项的范围却不是我们可以选择,而是由文化传统所决定或是在文化的脉络中进行的(林火旺,1999: 2)。
而自由主义与多元主义在社会的实践上有三个层次:客观、价值与实践。综观马来西亚情境,它很大程度上只停留在第一层次,即国家与社会虽然具有客观事实上的多元族群、宗教与文化语境,但对于第二层次上的“多元文化”之价值珍惜,则仍然存有极大争议,右翼民族主义势力仍然是主流,肯认多元价值的重要性、必要性与共生很大程度上只停留于表面上,而未充份落实到制度上、政策上,也即是第三个层次上。第三层次必须通过自由主义多元主义“承认/肯认”(recognition),而基本上金里卡的自由主义多元主义即努力于追寻对少数族群、移民社群“认同差异”的认可。由于“差异”造成了“肯认”上的冲突,他主张因族群各自拥有不同的文化认同对象,这需要以“承认”或“肯认”来解决。
如上所述,“肯认”必须回到第三层次的政治与政策之上,这其中又无法忽略宪政之设计,在这一方面,主张多元主义加拿大麦克基尔大学哲学教授詹姆斯‧塔利(James Tully)认为,现代宪政主义过度侧重普遍性与一致性,无法面对文化歧异性的事实,这亦是非常重要、可借鉴的理论视角。
“差异”与“承认”可以有各种思想资源的追溯,而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 有关现代认同(modern Identity)和“承认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的理论可说佔据其中一个关键位置(何怀宏,2019)。实际上,“承认”这一词汇自泰勒之后才成为一九九○年代以来政治哲学的关键概念,用以讨论与说明身份认同与文化差异的重要性,他将多元文化主义的核心思想直接表述为“承认的政治”命题,成为社会各种社会平等运动的动力,甚至取代传统政治哲学对资源重新分配的关怀。“承认”最早是黑格尔古典哲学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共同体之间、不同的群体之间在平等基础上的相互认可或确认。
泰勒从对自我认同的根源之探讨到认同的建构都与“承认的政治”相勾连,即在强调主体性的同时,他发现自我的形成和发展既离不开他者,更离不开他自己所处的社群。故此,泰勒的承认理论重视其对话特徵,他站在对话者的立场或社会立场来表达集体权利的诉求,把问题从“认同的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转向“承认的政治”(程广云、鹿云,2014: 5-6)。
一九九○年代中期,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与泰勒遥呼相应,他更深入的发展“承认”理论,描述了社会承认关系结构,把“承认模式”分为三种——爱、法律和团结,即分别体现于自信、法律承认与社会重视,同时指出“蔑视”作为“承认关系”的反向等价物(2005: 101)——包括强暴、剥夺权利、侮辱三种。霍耐特将社会进化的模式描述为:蔑视、斗争和承认,斗争是过程,蔑视是其动力,承认是其目标,从而阐发了社会承认关系结构(2005)。
然而必须说明,本书主旨不在于描述以上霍耐特所著重的理论问题,故未加以讨论,但其承认的模式与拒绝承认的伤害之论述其实都与本书所谈到的马来西亚华人不被承认及其问题有关。
本书主要是从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角度略援引查尔斯‧泰勒的“承认的政治”论述以阐释马来西亚政治与“马华问题”。泰勒的“承认政治”或可分成三个层面,即发现自己本真性的“自我认同”、与同类人群连结的“群体认同”,并确立自身所属群体的本真意识,而最后则通过文化的斗争和政治的手段实现他人与社会对自身所属群体的“社会承认”(何怀宏,2019;Taylor, 1994)。
泰勒与社群主义者认为,个人被深深地“嵌入”某些社群之中,自己所拥有的社群关系直接构成自我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归结而言,社群主义主张自我之定位须于特定历史文化脉络中寻得,自我不能像自由主义所主张那样具有充份选择人生目的及归属认同的能力(江宜桦,1997:85-110)。
实际上,马来西亚被公认与黎巴嫩类似,都是对其各族群人口比率最敏感的国家。在这两个国家中,族裔身份最具政治意涵,许多公共课题如选区的种族结构均与人口比率密切相关,使得国家具有一种百分比心态(percentage mentality)(孙和声,2017)。马来西亚的族群政治化与制度化使得各族群之间的族群身份之自我肯定,一直都处于强化的状态中,然而这种强烈的自我肯定却未形成完整的制度性承认(institional recognition)。
社群主义所认为的,任何文化群体的社会身份与地位都应该获得平等的“社会承认”,这对马来西亚是相当具有启示的。认同问题实乃任何社会最深层、最根本的问题,尤其在马来西亚的语境下,社群主义恰能解释本书论述对象的多元族群特质与结构。
当然,社群主义可能流于民族主义或为其所用,这是必须加以警惕的。但必须指出的是,社群主义者相对注重社会共善与个人自由之平衡,他们多半既重社群文化,也重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共同目的,甚至有学者认为二者之间并非可截然切开,而是相互补充(江宜桦,1997:106)。无论如何,不论平等自由主义、多元主义或社群主义,都强调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同时力主社会平等,只是一个要求“机会平等”,另一个注重“结果平等”。
此外,上述理论除了作为一种分析范畴,本书亦希望通过这些论述与理论资源,可以提供读者思考在马来西亚这个价值多元呈现、缺乏“公共理性共识”的社会中,究竟什么是“正当性”、“合理性”的基础。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不仅仅是对社会经济层面上的平等诉求,其出发点更是针对深层次的政治正当性问题。同样的,社群主义所坚持的差异认同的被“肯认”,亦是在追求一种群体性的合理秩序安排。
惟仍必须再强调的是,“马华问题”皆非西方学者及其理论可涵盖的。自由主义或多元主义尽管有助于一个更公正社会的形成,然而不管金里卡、泰勒等人的论述,都只针对西方的语境,他们在承认弱势者如原住民、加拿大法国后裔等少数群体时,却忽略了土著主义在成为国族/国家之后所形成的刚性结构所造成的压迫。
比如延伸来说,马来西亚虽也处于后殖民情境,亦已经历了去殖民化,但后殖民理论却未必适用。在西方后殖民理论中,尽管它探究“基于欧洲殖民主义的历史事实以及这一现象所造成的各种后果”(参阅罗钢、刘象愚,1999:2),并批评殖民者及其知识的压迫性,或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帝国主义,但却未充份注意到殖民地所造就的土著与移民社群的二元化性质,因此忽略了原住民的去殖民势力者最后却形成另一股步上殖民者后尘的国族宰制力量,对移民社群造成沉重的压力。
例如骆里山(Lisa Lowe)于2015年出版《四大洲的亲密性》(The Intimacies of Four Continents)虽重点批判西方“自由主义”在废奴之后,欧洲殖民者却又从亚洲与印度引进大量的苦力劳工,并没有带来真正的自由与解放,但土著原地主义论述及其权力宰制同样不在其视野之内。
三、本书架构与研究思路
本书所有文字皆与“马华问题”有关,因此本书第一编“独立建国时期:马华问题的历史根源”先集中讨论“马华问题”及其根源与本质,并将时间点紧扣于一九五○年代马来西亚独立建国这一“关键时刻”。谓为“关键时刻”是因其具有巨大的历史辐射力量,对后人产生决定性影响,而今天华人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即系于此。
首章〈原地主义与华人的“承认之斗争”的源起〉先阐述马来西亚华人所面对的最基本问题之根源——“原地主义”,而这一问题自英国殖民时代华人大量移民马来亚即已启始。笔者以“原地主义”指谓“因土著身份而获得特权”现象,这一主义的立足点在于强调“土著”与土地的自然关系,而它之后再顺延至马来西亚建国之后,并实质进入国家宪制与体制之中,故讨论马来西亚华人问题不得绕过这一根源。
本章尝试从历史的纵向视角切入,并借用上文提及的一些有关社群主义的少数群体及其处境之研究论述,尤其是泰勒的“承认的政治”理论所提供的进路,以解剖华人社会作为移民社会后裔在“原地主义”操作下“不被承认(nonrecognition)/要求承认”之根源及其所造成之困扰与影响。原地主义与华人社会“不被承认”之困境实乃一体之两面。
第二章〈徘徊于独立大局与平等困局中的华人社会〉,讨论了独立运动时期华人在面对这一其来有自的“原地主义”之顺延时,所经历的争取与斗争运动,他们夹处于“国家独立”与“族群平等”之间而不可兼得,面对了某种程度的张力。在殖民宗主国即将撤退之际,他们欠缺政治法统与现实实力,因此所谓的“独立”或“民族自决”往往不在他们“天赋”的平等权利之中,这是少数族群与非土著移民的悲剧,也预示了之后数十年他们在马来西亚的政治地位格局。本章通过当时的中文报刊舆论,探视华人社会在“独立建国”的时代大局、大蠹下,其所得所失与进退失据的处境。
而第三章〈马来民族主义与“解放”“独立”的本质〉则是在上一章的基础上,从近代“民族自决权”与“民族解放”思潮脉络进一步聚焦于追问“独立”与马来民族建国力量的实质,指出二者之目的不在于追求个人自由与民权,而是以“民族”解放为鹄的。通过省思“独立”之于国家的意义,我们可以叩问当年响彻云霄的“民族解放”口号意味著什么?尤其是马来亚之独立,对于作为非土著和少数族群的华人社会又意味著什么?
宪法是一个现代国家的基本治国大法。故此,马来西亚华人问题之被制度化必须回到宪法的层面去理解,第四章〈“宪政时刻”中的族群纠葛与宪政阙失〉处理了这一问题。实际上,宪政认同之建构对多元族群国家尤其重要,因此,立宪基础的关键并非去寻根或寻求原生血缘和族群意识,而主要是应考量赋予人民普及公民权,以促进公民不分族群地向国家归属与整合。
然而,在一九五○年代的马来亚独立宪法拟定之过程中,却嵌入了过多的族群化想像与血缘历史论述,使得马来亚宪法烙印著族群主义多于上述公民宪政精神。作为研究途径,本章也主要通过当时华文报刊中所呈现的争论与语境,以探讨马来亚独立运动时期族群认同及政治权益博弈对立国宪法的影响与冲击,如何使得宪政认同建构失去了先天条件。
此外,本章聚焦于李特宪制委员会(Reid Commission)所提呈的“李特宪制报告书”及随后的争议与修订,乃至马来亚正式宪法确立之过程,并尝试以思想史的角度分析此过程中所揭示的马来亚宪政阙失,以及种族主义大潮与各族之间的宪政创造力量及资源之匮乏对马来西亚宪政进程的戕害。
本章亦将借用上述格雷的多元主义的自由主义视角检视“李特宪制报告书”,最后将指出种族主义与宪政之间的严重矛盾与紧张关系,并因此预示了马来西亚宪政之路的维艰与难行,也宣告族群主义制度化后的难解。
第五章〈政治变动下的华巫关系与次族群间之整合〉则是处理马来西亚“原地主义”底下另一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族群/种族问题。在一九五○年代马来亚独立运动期间,马来亚此一英殖民地正大步迈向立国之际,英国人即将撤离,而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则正在为新兴的国家建构方向争论不休。由于在英国统治底下,马来亚复杂的族群结构被化约为所谓的“三大族群”单位,而在独立建国前夕纷乱的政治博弈之中,族群利益也主要以此为分配及谈判单位。
本章以此脉络为研究进路,著重探讨在这段关键及高度政治化的时期,华人社会与马来族群在权利竞逐下(也略提及印度人社群),两方互为他者,内部次族群(/方言群)之间的关系如何产生整合及其演化。过去的研究都较著重于整体华巫之间的关系,而忽略了这两大族群内部的复杂性。本章将揭示华人与马来族群互为他者的族群建构性面向,说明政治变迁与族群博弈如何一方面强化了两大族群内部原已在发生中的内聚,一方面又淡化了内在差异,并兼论人口普查族群分类在其中之作用。
本书第二编“独立建国之后:平等追求与文化困局”则主要具体探析了“原地主义”所辐射的各种问题,而这首先必须先追溯马来西亚独立之后所发生的、最划时代的大事——“五一三事件”——这是因为此一事件强化、固化了已然的族群不平等。1969年5月12日全国大选乃两大族群争夺国家机器的高潮,但最后却以暴动与国会终止运作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族群政治失衡告终。
第六章即以〈“五一三”之发生、记忆政治与华人的受创意识〉为题,一方面对各方各族的记忆分歧现象做叙述,以勾勒“五一三”的不同理解,另一方面也将揭示“五一三”记忆已成为一种记忆符号,为官方所使用以及其对华人社会所造成的冲击。“五一三”之后,不仅是事件过后的整个一九七○年代,也不只是八○或九○年代,至今它依然时而继续在政治变动的裂缝之中浮出历史地表,作为最具恐吓性和政治工具性的历史幽灵复活于大马社会的各个死角。
对华人来说,华人在“五一三事件”中受到的创伤乃国家机关与政客、暴民的有机结合之结果。自“五一三”以后,华人普遍上更深化了对政府的不信任态度,虽然华人另一方面又希望争取更多的政治权利及国家机关在各个领域的资助,因此可以这么说:华人觉得国家机关终究“可爱而不可信”——可爱,因为华人需要政府的资助;不可信,因为国家机关的滥用。如上所述,国家(state)与华人民间社会之关系是一个重要议题,将在此章稍做处理。
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终究逃不过当下的影响,官方的“五一三事件”阐释亦进一步具体化了“原地主义”为更具族群性的现实政策,如一九七○年代修改宪法以固化马来人地位与“新经济政策”的执行。客观的说,“五一三”使华人陷入长期的政治从属地位与难以解魅的记忆恐惧之中。
第七章〈“五一三”戒严中的华巫报章叙事与官方论述的形塑〉则通过对当时的中文报《南洋商报》与马来文报《每日新闻》(Berita Harian)之研究,管窥“五一三”戒严时期的言说空间以及此一空间限度与族群政治环境下所形塑的不同记忆与叙事型态,揭示中文及马来文报刊叙事的差异及他们在马来西亚记忆政治形塑中所起的作用。这其中尤其关注它对官方论述与记忆塑造的影响,同时也将考察在戒严下,报章叙事中所呈现的一些官方行为与人民日常生活,以窥见日常生活实践所透露的“弱者的实践艺术”。
“五一三事件”之后,除了“新经济政策”贯彻了强烈的原地主义实质,各种文化、教育政策也一样雷厉风行,马来西亚华人社会面对了更为严峻、凛然的“平等”问题。第八章〈“平等”与“公正”:分歧的华巫族群社会正义观〉阐述了这一现象。自一九五○年代马来亚独立宪制之拟定与谈判时期开始,出于族群利益分配之博弈,公平、平等这些属于“社会正义观念”的词语也夹杂在族群动员之中,充塞于马来西亚各种政治文字与社会话语之中。
如上所述,马来西亚的最基本问题是种族问题,社会的利益分化和对立往往都被族群化,而阶级问题则相对被模糊化,这使得族群之分歧造就了对“社会正义观念”的不同视角及诠释,进而形构了相异的社会正义观。显然,对任何一个现代国家而言,不管对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体制,如果要稳定和持续发展,都必须表达基本的社会正义。尽管此议题及概念如此重要,但有关马来西亚社会之内的正义观之研究似乎阙如。
本章尝试通过独立以来国内两大族群,即马来人(尤其是以长期执政的巫统为主的主流民族主义者)及华人社会的几个相关概念如平等、公正及公平之论述,探讨马来西亚社会内的正义观之历史起源、本质及其演变,并从罗尔斯的平等自由主义视角对之进行初步评价。
在很大的程度上,马来人原地主义与特殊地位论述主要建构于历史因素之上,那么在历史统绪与华人所追求的普遍价值——平等价值——之间,应当如何兼容?两者之间应如何维持适当的限度?这实乃马来西亚华人必须面对的大问题,本书第九章〈历史统绪与平等价值之间:华人的多元文化追求向度〉尝试探视此议题及争论,通过华人社会在文化(尤其在教育)上的平等诉求之目的和型态切入,概括地检视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对马来特权所能接受的限度,同时揭示华人社会所追求的乃一种多元文化主义的向度,并没有完全否定国家的历史结构。
延续本书有关马华社会在宪法与文化权利上之阙失脉络下,作为“代结论”,本书最后一章〈国家权力边缘下的马华文化记忆传承与文化再生产问题〉将通过历史记忆传承的途径分析马华社会文化的发展,并将其与国家权力相关联进而考察华人文化建构与国家互动的型态,从而反思在集体记忆传承过程中所面对的种种挑战及因应而来的曲折演变。
本章将尝试追问:作为一个移民社会,其移民性如何主宰它的文化取向?在失却有效的国家/官方机制与管道,甚至面对国家意识型态与国家机器之压力下,华人社会长期以来仅靠民间体制力量如何维系及传送其集体记忆,并呈现怎样的性质与归趋?
同时,本章也将从自由主义在对文化族群权利的争论中所论及的文化赋权及少数族群公民权利论述,尤其是有关国家机关及公共语言对文化发展之决定性作用方面出发,检视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文化权利及其对华人文化发展之限制。
具体而言,文化权利涉及国家对族群文化之肯认及文化资源之分配正义,而这以文化族群是否能有效地、创造性地参与自身文化,并具有传承、再生产族群社会文化之能力为基准。本章借用上述论述之启示,指出在既有的宪制及文化政策权利下中文在公共领域之使用,以及华人社会的中文习得程度与焦虑,揭示华人社会文化重建之理想必定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最后,作为本书总结,本章也约略讨论这些问题在当代全球化与后现代情境的冲击下,所呈现的一些现象与变化。
四、结语
概而言之,本书贯穿了一个问题丛聚,但牵涉到两个语境。其一即自殖民地时代至独立后的历史语境,另一个语境是属于当代性的,就是晚近二十年左右马华社会的思想、政治与文化状况。
笔者希望对这两个总体状况做一个关联,使本书语境即是历史的,也是当下的,以理解本书所关怀的问题——“马华问题”。作为马来西亚华人,不免自我地进入了这两个语境状态之中,这就是笔者上文所说的研究态度——马华问题既是生活处境的问题,也是一位学术人员必要的学术关怀——这也是笔者始终认为的:学术人员在时代转弯当中都应该具有自身的问题意识、关怀、态度与定位,但在另一方面,作为学术人员,这又是一个历史问题、学术上的客观研究问题与对象。
实际上,已故前辈学者骆静山多年前曾指出,马华社会对其自身复杂的问题缺乏深刻理解(1994: 77),因此真实理解更是每一个华人的挑战。作为一位中文学术人员,其本份及使命就是寻找一种属于自身问题的一个解释构架。对自身问题的理解,更离不开一套学术语言、术语的建构,以通过此一术语、架构了解自身、阐释自身,这可说是本书的另一个初步尝试与初衷,更希望能藉此提出解决“马华问题”的某些思路。
读者或可从书中知悉,笔者尝试揭示及贯穿一个基本的立场,即解决“马华问题”在于必须超克移民后裔与少数民族文化所普遍既有的卑微姿态、心态,并以公民与自由主义的公共角度去追求“承认”——追求超越族群权利的普遍权利,因为后者其实即已包含了前者——人类最基本的自由、平等与多元的生存保障。
最后必须说明,本书各章都曾发表过,但已做了不同程度的修订或增删,同时增加了参考资料、统一格式及减少重复,其中第九章和第十章做较明显修改,包括纳入了另一篇单篇论文〈马华社会文化权利及其文化再生产〉(请参考附录“原文出处”)。然而,由于本书围绕著相关议题而论,加以当初是以论文的形式慢慢、逐步发表的,文章内容间仍有重复之处,这一点还请读者们包涵。
(初稿于马来西亚“抗疫行动限制期”,2020年4月25日;定稿于2021年9月13日)
许德发,马来西亚霹雳州吉辇角头人,马大中文系毕业、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为马来西亚苏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学中文学程主任、高级讲师与华社研究中心学术董事、《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编委。曾任华社研究中心研究员、台湾汉学研究中心访问学人。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马来西亚华人历史及政治、文化研究,近期较关注于早期马华文学、思想及南来学者研究。
编按:本文原为许德发《在承认与平等之间:思想视角下的“马华问题”》一书之导论,原题为〈“马华”作为问题与研究的态度〉。
本文段落有所调整,以方便网络阅读,其余没有更动。本文获得台湾时报出版社授权转载,谨此致谢。
本刊近日也将刊发该书的两篇序言,分别由马来西亚资深作家张景云先生与台湾学者钱永祥先生撰文,敬请垂注。
欲知该书详情,敬请点击此书介。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